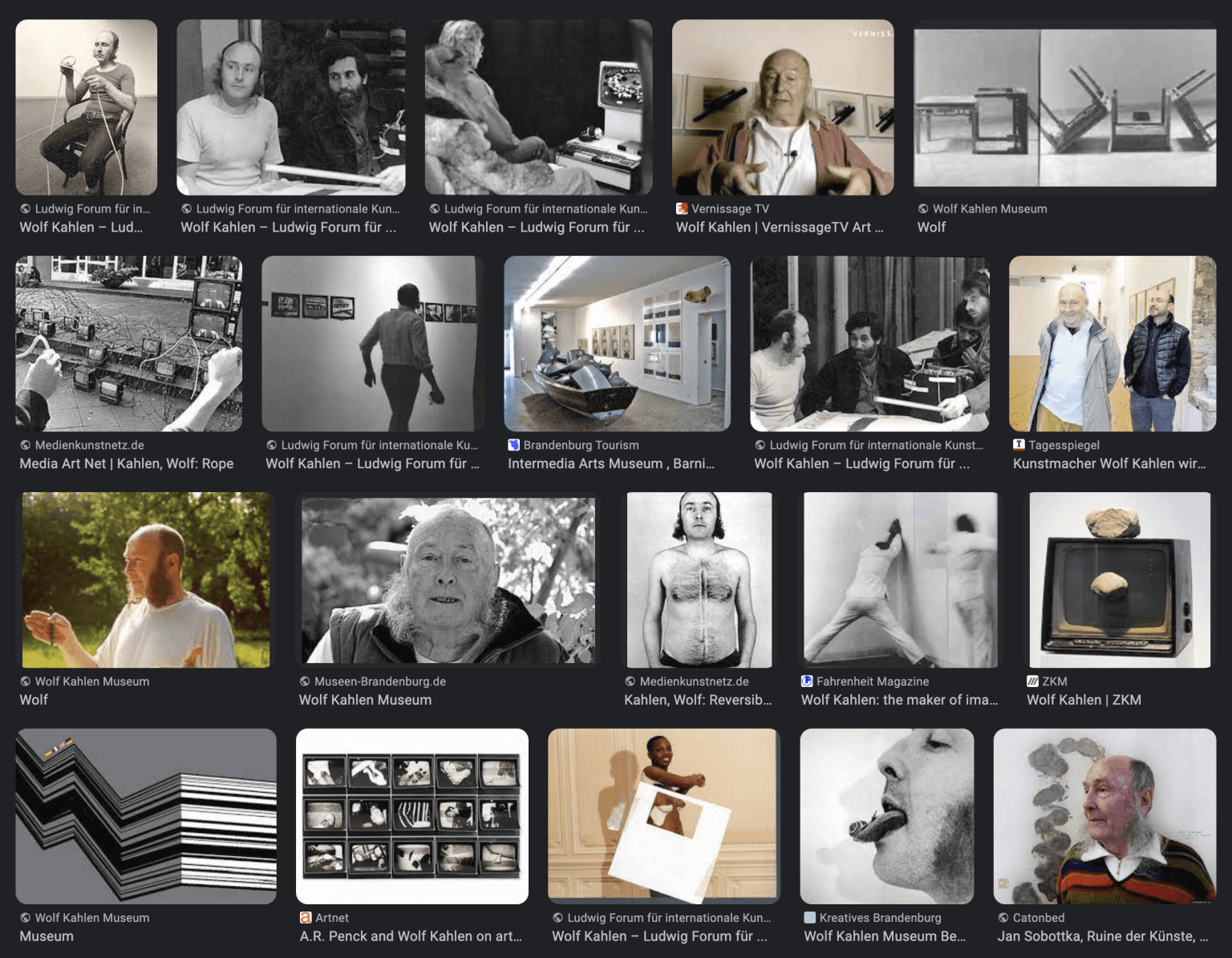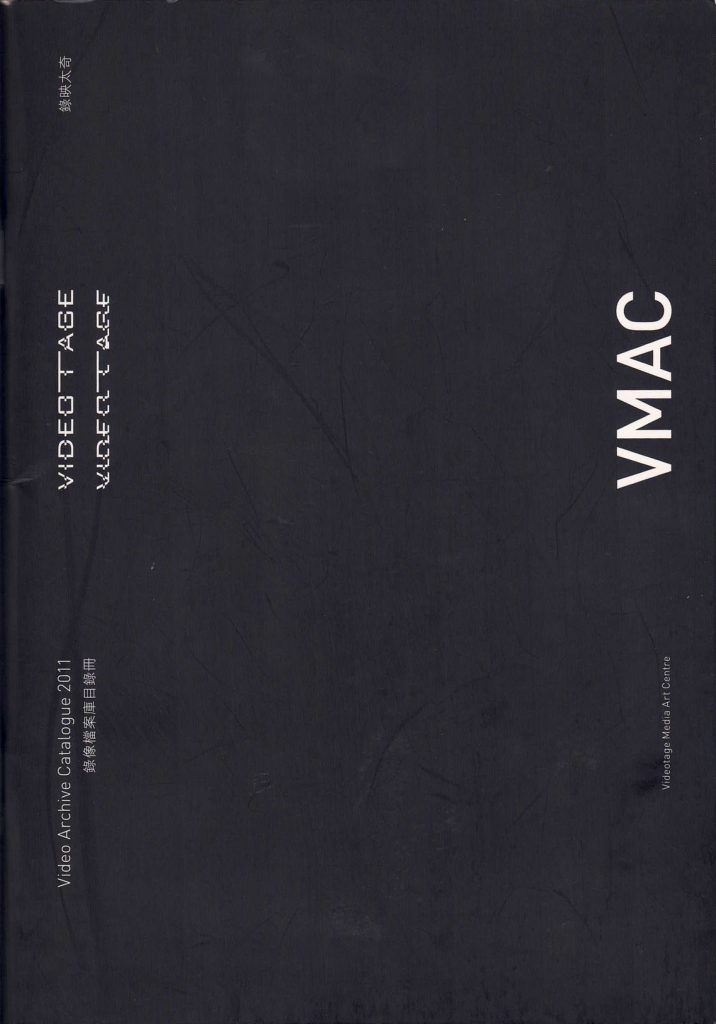October 2023
VMAC文章
《用鏡頭思考:錄像就是當下的存在》
撰文:Wolf Kahlen(n.b.k. Video-Forum 委托)
中譯:陳琸錀、黃小燕
別忘了,「Video」一字源於拉丁語,意思是 「我看」,是現在時態,不同於「我看了」或「我看過⋯⋯了」。錄像不是要回望過去或保存事物:它誕生於當下,亦是為了當下而存在。錄像就如1960 年代末大眾汽車廣告中的汽車一樣:它跑啊跑,跑啊跑。(譯按:原文run,同時有跑動、轉動、播放、運行之意。)當年錄像技術帶來嶄新的官能體驗,我至今仍歷歷在目;現在的錄像卻少了這種衝擊,因它名副其實地被「壓縮」,而變得扁平化。
當下的存在是錄像藝術的原始資本:攝像機轉動時,屏幕會——即時或稍稍延遲——顯示正在發生的事情,不論是發生在我們面前的事情,或是我們看到自己。如今,錄像只是一種媒介的稱謂,影像紀錄已屬常態。然而,觀眾還是能感受到實時與預先錄影的現場直播是多麼不同。即使是現在,電視節目還是會特別標明「即時直播」的影像。錄像 (recorded images) 是獲取知識的工具,可以是高水準的培訓教材;錄像藝術 (video art) 則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價值,當中最能突顯到錄像媒介特色的,是以閉路電視為軸心的錄像裝置作品。這類作品在攝像機和觀看影像之間保持著直接的連繫。正如斯拉夫科.卡昆科(Slavko Kacunko)所說,閉路電視的本質在於影像的即時傳輸。(譯按:此處原文為 “when television is involved”,Television中譯「電視機」,其字源「Tele – vision」具有遙距視訊的技術涵義。)
在印度,傳說某位瑜伽士有著這種能力:他可以將網球的內面翻到外面,外面翻到裏面。在大眾汽車推出「跑啊跑,跑啊跑」廣告的1968年,亦是卡式磁帶成為最流行的媒介的年代,它轉啊轉,轉啊轉。它如莫比烏斯帶般奧妙的構造超越了單純作為科技發明或數理現象的存在,反映了我們對逆轉和永恆的渴望,是名副其實的藝術品。作為意象,它與印度瑜伽士的內往外翻網球一樣令人震攝。錄像藝術品同時是物體,它實實在在呈現於我們眼前,其事實性的存在與現實中一切其他事物無異。「事實」是行為的結果,錄像藝術品亦是行為的結果:在影像播放過程中引發的思維過程所產生之結果。當然,這首先是由感知過程引發的,再之後是印象。錄像可以是思想的事實。它可以,而且應該如此,這是我作為1960年代末的錄像先驅者的看法。畢竟,藝術作品是思考的工具。我們同時思考可能和不可能(像我們從莫比烏斯帶和外翻網球中得到想像「不可能」的靈感),其中還穿插著思維的對應物:感覺。「既存在同時又不存在」的想法回應著我們對世界的深刻體會,卻被理性思維所摒棄。然而,「皆是 」和 「又是」(Both/and) 是永恆不變的現實。就如地球是圓的,因此風景是無邊無際的;撇開障礙物不談,它們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風景是連綿不斷的,包括空間上的、時間上的。這正是大自然的魅力所在:它生生不息的同時,又不斷經歷著死亡與復甦;它的時間如洪流般流動變遷,如同我們的存在本身。我們總是思疑自己死後是否會於來世重臨,或是會在何某處繼續存在。歸根結底,這是我們對逆返的盼望。
1969年,我構思我的第一個錄像藝術計劃,當中共有15個概念,我統稱它們為《逆返之旅》。當時,巴鬆・布洛克(Bazon Brock)立刻反駁我:沒有甚麼是可逆的。也許他是從物理學出發,那沒錯,只是視野太狹隘了。後來他改變了想法,1987年,我讓他在我的《柏林藝術廢墟》上朗誦他的「廢墟理論」時,他有截然相反的想法。「皆是」和 「又是」始終存在,然而它激起了我們的恐懼,歸根究底對死亡的恐懼,因此我們才會囤積物件,或是依附他人。但同時 「皆是」和 「又是」又代表了真正的自由:我們需要對現實有真正的認知,才能感知它、接受它,甚至培養它。 這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現實不是雙重的,當然也不是數位化的。佛家有「萬物」之說: 一即一切,「一」既是萬物,也是唯一的「一」。萬物既是 「一」,也是自身。這是思考的藝術。各種類型的藝術家都是影像的塑造者、影像的傳遞者、影像的創造者。永恆的藝術通過我們的眼睛、耳朵、思想、行為、味覺、平衡、能量、熱和冷等 27 種感官,以影像的形式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這適用於科學、哲學、醫學、建築、設計、時尚,以至烹飪領域的所有創造形式。安全別針和炸薯條的「創造者」都有各自於腦海中的影像。不論是「我思故我在」或是「E=mc2」,它們首先是一種影像。在物理學和數學中,人們談論所謂優雅的解決方案或模型,其實,它們不過就是影像而已。
留存的錄像代表了留存的影像,它最佳的呈現不是作為形式的影像,而是作為「力場」的影像。它會「跑」,有播放時長,但不代表它是線性的。錄像創作者不是資訊的提供者,更不是影像的開發者。轉動的錄影帶如事實一般發生,它的運行使其成為時間線上的行為事實。它不需要呈現動作,亦不需要講述故事,因為電影早就能在這方面做得更好。在我看來,錄像是有著獨特的可能性,它可以透過時間來調整、帶領、甚至誘導觀眾,營造思考的氛圍,在其之中創造力場 (FIELDS),而非創造「點」或「線」的串列式印象。思想會使人感動、不安、困擾或是堅定。磁帶作品,或應說「屏幕作品」,可以將觀眾的意識帶到冥想的元點,亦能因撼動觀眾而使他們膽怯卻步,寧可停止思考,讓思緒不受控制的任意蕩悠。
一部好的錄像作品可以讓觀眾任意蕩悠,只要觀眾一直坐著,就不會錯過任何東西。作品的核心與觀眾之間形成直線般的專注,開闊的力場會製造強烈的感受,觀眾仿如被纏於蜘蛛網中。以1973年作品「TAU」為例,當中記錄了以雙手扭捏繩子所產生的張力和釋放,這是自然的定律。當然電影也能做到張力和釋放,不論是以陳述的、關聯的、甚至是抽象的方式,這也是電影創作者一貫所追求的。(電影史裡有不少優秀的「抽象電影」,但它們本質上都是帶叙事性的抽象。藝術史還是對此有著嚴謹的區分。)
從一開始,這種區別就使「加洲的錄像」和「東岸的錄像」有所不同。翻閱美國錄像的書刊,你會立即注意到其中相異之處。至於歐洲錄像作品,雖然有著相當的質素,且在1970年代後期開始受人注意,但在美國的錄像圈裡,它們仍然未公平地獲得足夠的關注。例如在1977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策展人芭芭拉.倫敦(Barbara London)將我的錄像作品收錄於「來自柏林的藝術 」展覽之中,這一糾正措施仍沒能帶來甚麼改變。在美國的教育制度,「美國優先」已深根蒂固;錄像藝術史需要重寫,但這不是我今次想探討的。
1965至1966年間,我在紐約遇到了格式塔心理學家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自此,我們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他到訪我設於新澤西州的工作室,從這裡可以俯瞰曼哈頓城區。我的第一部 UMBILD 佔據了整個房間:一個直徑三米的燈罩狀圓桶,只有彎腰才能進入。從外面看,它就像一個圓柱體。它的內部是一塊畫布,給人一種方形房間或無定形空間的惑人錯覺。我想藉此面對「外部和內部的不同感知」,而這就需要「時間」此材料,像在電影、文學和音樂中一樣。阿恩海姆和我都對此很感興趣,他立刻明白「同時性」在其中的作用,而不要在內部圖像中創造一個「序列」的同時,要創造一個全方位的「時空存在」是有多難。1966年,我在紐約舉辦展覽時,他在展覽圖冊中提及此事。即使在他103歲去世前不久,他對此仍記憶猶新。
阿恩海姆是位獨具慧眼、專注於藝術感知的格式塔心理學家,今天人們會稱他做媒體科學家或媒體哲學家。在 1932 年出版的《作為藝術的電影》一書,他指出了感知和認知的基本過程,這與後來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之論點甚相似。他明白我想要甚麼:將外在形式與內在形式,像印度瑜伽士的網球一樣,結合起來,儘管這是不可能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處於它面前,進入它,置身其中,之後又置身其外,獲得「皆是」和 「又是」地並存的體驗;那並非去體驗一種而是多種現實。(「沒有單一現實,只有眾數現實」, W.K.,1982年。)阿恩海姆確切讓我警覺,若不把影像當作一個包圍自身,充滿重力的思想力場來體驗,而線性地將其理解為繪畫式的幻覺空間,是多麼危險。
那時,我還沒有任何關於錄像的經驗,但我在工作室裡用過一台老式美國電視機的小圓屏幕,並將電視上的內容鏡像傳輸到我的房間裡。我沒把它當作一件藝術品,而是一次愉快的實驗,那時我剛開始接觸閉路電視這媒介。幾個月後,我有幸拜聽了麥克盧漢的演講,他印証了我們全新、充滿洞察力的世界觀。那時還沒有互聯網,也沒有被數碼簡化的世界,但他清楚地預見到,我們意識中將經歷的根本性的變化,那不是物理上的改變,而是心理和感知的動蕩,有如感官層面的山崩地裂。因為,我們將 「墜入」無地域和無時間的境況,而我們對此毫無準備。我們沒有認真看待並接受世界的真實,包括它的無邊無際和一切事物的流動性。他還預視地球村的出現,虛擬錢幣作為「媒介」,還有濫詞和謠言的當道,如此等等。
當時的藝術家如安迪.華荷(Andy Warhol)對於媒體的理解,比今天的許多錄像藝術家還要深入。華荷在 1965 年 3 月首映、長達 8 小時的影片《帝國大廈》,實際上就是一部沉思式的、「跑啊跑」的錄像。1963 年,當華荷拍攝《吻》這部長50分鐘、「無始無終」的電影時,我相信他恨不得有像錄像這樣的媒介。在藝術層面,錄像更可以是一種認知工具,但只有寥寥可數的藝術家做到這一點,而今時今日大多數的錄像藝術家都沒有走這條新道路,他們所做的僅能以「新瓶舊酒」或「舊瓶新酒」來形容,畢竟,錄像早是個年過半百的媒介了。他們使用錄像來敘事,來描述事實,但不論是以線性或虛擬或超現實的方式,電視和電影早已經可以做到這一切。
歷史上的各種媒體和媒介,兼為人類拼命追求,且於未來仍歇力求新的「感官延伸」(麥克盧漢稱為「身體的延伸」)都印証,由發現鏡中的映像起,我們一直慢慢卻無疑地偏離陳述現實,而不是像某些人反復聲稱的那樣接近「終極的真實」。不論是帶味屏幕(smelling screens)還是自拍,都無濟於事。如今(2021 年)的電視影像如此清晰、對比度如此之高、色彩像無加修飾的如此絢麗,以至於感官豐富的觀眾會產生錯覺,以為自己越來越接近現實,但同時又被「推進」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萬綠叢中一點紅」,越來越不真實甚至超現實的世界。因此,人們也就更順理成章地想要沉浸於更加「不可能」(虛擬)的世界了。換句話說,資產階級所夢想的超現實主義世界(今天稱之為 「虛擬」世界)—— 終於(不幸地)成為了現實。這是一個危險的動向,而我們正因此而漸漸「從地球上消失」。
編注: 此文節錄自德國錄像先鋒藝術家Wolf Kahlen為n.b.k. Video-Forum 五十週年(2021)所撰寫之文章。節錄獲作者及n.b.k. Video-Forum 授權重刊,特此致謝。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僅代表作者本人,並不反映VMAC的觀點。)
員工精選
《錄像檔案庫目錄冊》,2011
自2008年起,錄映太奇開始著手處理機構內的錄像藝術資源。2011年正式開放數碼化修復的檔案庫,並製作了這一精選目錄冊。
同年,文晶瑩、鮑藹倫和蔡海盈先後用VMAC的影片資源,以「香港實驗短片」、「自家制影片(Homemade Video)」和「週年紀念」為題,策劃了一系列巡迴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