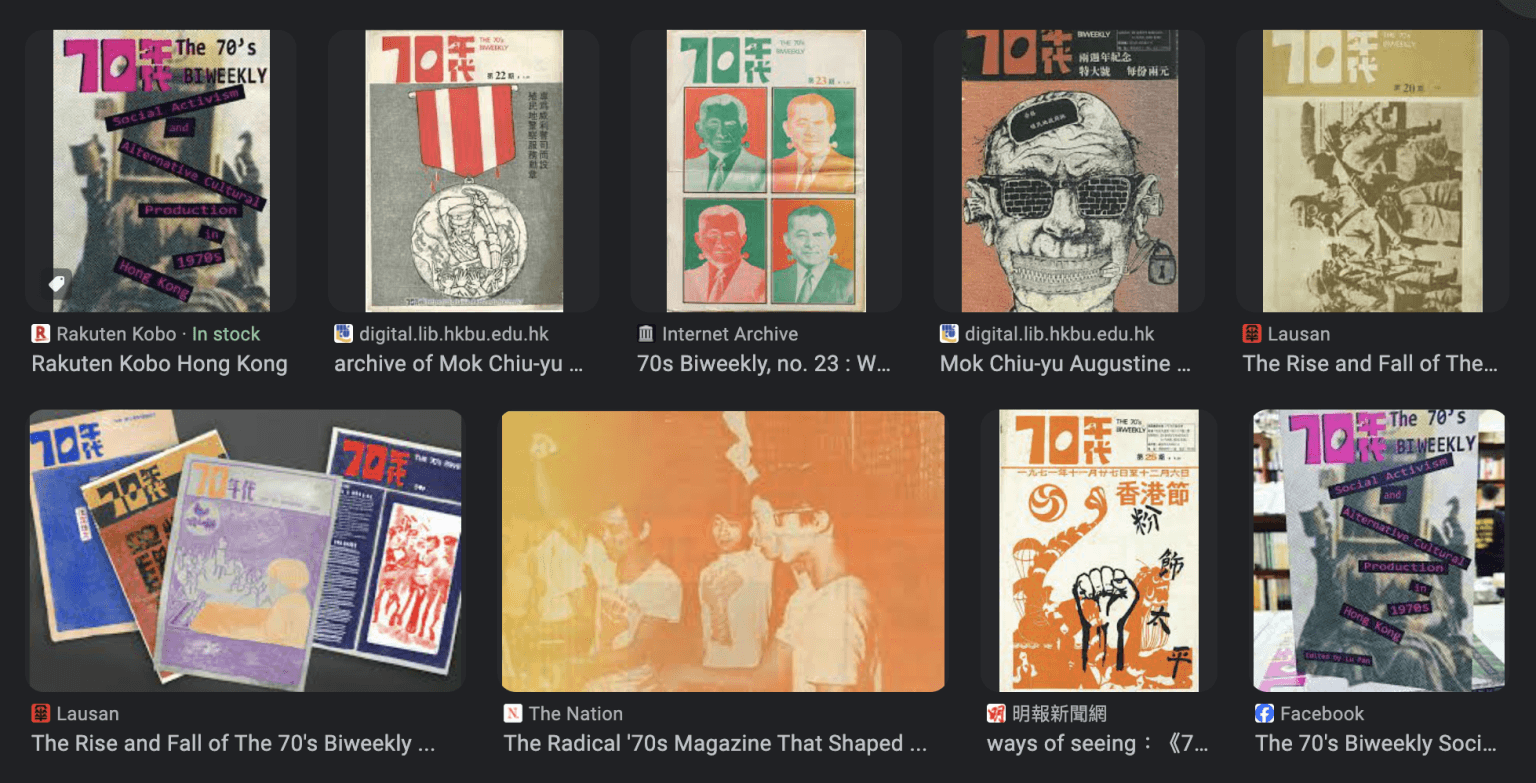December 2023
VMAC文章
《70年代雙週刊》及其政治電影實踐 (節錄)
撰文及翻譯:蔡倩怡
本文探討源自《70年代雙週刊》(下稱《70年代》)的政治電影實踐,並將其形成的文化生產與雜誌的政治行動互相連結。目前關於《70年代》的學術研究和討論大多集中在其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行動方面,如關注香港身份的塑造以及莫昭如和吳仲賢等編輯委員會成員的劇場實踐。因此本文試圖擴大對《70年代》的研究範圍,著重於《70年代》相關的電影實踐,並視之為文化生產,以及審視其如何在1970年代香港的文化冷戰和殖民統治結構中將電影藝術與政治意識形態和行動結合。這裡的研究對象——「政治電影實踐」所指的是由《70年代》發起的電影製作和流通,其中包括編輯成員進行的政治電影製作,尤其是1971年的《香港保衛戰釣魚台示威事件》和1978年的《給香港文藝青年的信》;以及電影團體的形成,如土佬福電影會、影視系統和仙人掌等,這些團體構成了一個另類的地下電影群體,引領了一種新的集體文化模式。這些實踐不僅與他們對全球反文化運動、無政府主義、國際主義和進步左翼意識形態的認同密切相關,而且還從另類與多元的敘事和觀點中闡明了香港文化的形成,突破了多年來壟斷了有關香港文化冷戰的歷史論述。《70年代》的政治電影實踐對於重新探索本地文化史具有重要意義,並能回應香港電影實踐與日益加劇的政治場景之間的關聯,以及重新思索文化冷戰中二元對立的常規話語。
1970年9月11日,由大影會舉辦的「業餘電影節七O」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展示了一系列實驗作品,其中包括石琪和吳宇森合導的《死結》(1970)和羅卡的《乞食》(1970)。根據零散且有限的文獻檔案,這可能是公開展示本地實驗性影像作品的最早場合。對年輕的莫昭如來說,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實驗電影」或「香港獨立短片」的雛形。正如他在《電影雙周刊》中所述,他開始意識到「有一群知識分子製作了無聲黑白的實驗電影」[1]。 一年後,他邀請了羅卡和趙德克拍攝捍衛釣魚台運動期間的示威活動,並製作了紀錄片《香港保衛戰釣魚台示威事件》。這部電影出於意識形態目的而製作和流傳,標誌著《70年代》的政治電影實踐中批判性轉變的開端。莫昭如通過持續的社會電影實踐來質問「電影」的定義,包括與《70年代》的編輯團隊共同發起獨立的電影會,並拍攝了另一部實驗短片《給香港文藝青年的信》,以質疑在如此社會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形塑。這些電影實踐與《70年代》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從出版角色擴展到電影領域,擴大了其文化行動和社會參與。因此,本研究的核心問題由此開展:從《70年代》的角度來看,電影在美學、文化和政治領域上的認知如何交織?他們對電影的認知如何與《70年代》的文化行動和意識形態立場扣連?在1970年代的文化冷戰和殖民統治的背景下,這種文化生產如何折射了香港文化脈絡的批判性轉變?
由於歷史文獻與檔案有限,收集和取得與《70年代》及其政治電影實踐相關的研究資料並不容易。即使1970年代的香港被稱為「麥理浩時代」,代表了香港文化史上的範式轉移和身份形成的過渡階段,有關《70年代》以及其作為香港文化生產的重要場域與政治電影實踐的研究仍然不足。在香港研究的最新學術著作中,有一種對於1970年代和麥理浩時代框架為主流論述作重新評估和批判的趨勢。例如呂大樂重新審視了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以及1967年暴動後的社會改革[2]。呂大樂認為,麥理浩時代的社會改革不是對地方性或英國與殖民地之間協商的回應,而是受到策略性冷戰議程的觸發。此外,馬傑偉將香港描述為「衛星現代性」[3],符合自1970年代以來的跨境文化政治。 Florence Mok通過「隱蔽殖民主義」框架[4],探討了殖民政府在1975年引入的Movement of Opinion Direction(MOOD),以「彌合公眾與殖民政府之間的溝通差距」(尤其是在1967年暴動之後)為由,來監視港人社群中的輿論及民意。
在研究1970年代香港或麥理浩時代的主流論述中,顯然不足以探討香港在七十年代的文化和社會構成。儘管這些學術研究指出,關於1970年代的論述仍有待探索,但它們更集中關注流行文化、身份認同和社會政治背景的軌跡之間的互動,而對於另類文化及其在文化政治和行動主義中的表達,特別是與《70年代》的關聯,則一直被忽視。《70年代》的地下流通及其反文化、無政府主義和行動主義的方式,並不被大眾廣泛接受。在這個層面上,對於《70年代》在廣泛的本地文化史論述中備受忽視,可以歸因於檔案保存和可見性不足的政治因素。這與香港研究的主流敘事一致,其敘事形塑建立在中國民族主義、殖民統治和香港的邊緣地位之間的相互關係之上,而獨立電影和文化行動主義等另類文化生產,則超越了香港研究的固態論述模式,因此被忽視了。因此,本章的結論將對於另類文化生產的缺席進行反思,以重新審視這種論述形成過程中的文化政治。
作為香港文化史範式中具有文化行動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意義的象徵,《70年代》在香港的文化歷史上佔據了開創性的地位。《70年代》並非承接源於左翼或右翼政治陣營的文化傳統,擴展了與政治行為相關的文化想像力。即便如此,此研究亦無法將研究主題與1960年代的文化遺產完全獨立分割,尤其是與《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部及知識份子的關係,以及1960年代的影迷文化和電影會的聯繫等。從社會人文的承繼和電影對社會政治結構的回應角度來看,最初被部署為軟性文化宣傳以獲得社會影響力的《中國學生周報》,一般認為與右翼政治議程保持一致,並在冷戰期間成為香港文化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括在下文將要研究的影迷文化和電影會。六七暴動後,《中國學生周報》經歷了一次轉型和本地轉向,開始形成一種與冷戰的二元框架脫鉤的嶄新認同感。因此,《70年代》沿著《中國學生周報》所傳承的本地轉向軌跡,將其重新配置為對政治烏托邦主義和文化行動主義的新的尋索。作為文化生產場所和傳播政治意識形態的接通載體,《中國學生周報》和《70年代》都是香港文化歷史中的關鍵出版物,並共同探索對電影的多元認知。通過現代主義等西方文化趨勢的棱鏡,從《中國學生周報》衍生出來的電影實踐修正了對電影從娛樂到電影藝術的認知和理解。《70年代》則以社會定位甚至具有挑釁意味的政治行動的基礎來看待電影實踐。這種分歧揭示了它們在文化冷戰中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位置,以及對電影實踐的不同想像。因此,本文會從1960年代末期的另類電影實踐開始,並對與之相關的《70年代》的電影作品進行批判性分析。
注釋:請參閱英文版。
此文為節錄,原文刊於《70年代雙週刊:香港七十年代的自主媒介、社會行動主義及另類文化生產》,潘律編,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23。)
[1] Li, Yu-si (as the pseudonym of Mok). “Ni rengfou xiangxin dianying keyi gaibian shehui? (Do you still believe film can change the society or not?)” Dian ying shuang zhou kan, no. 49 (1980), 24.
[2] Ray Yep and Tai-lok Lui, “Revisiting the Golden Era of Maclehose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forms,” China Information 24, no. 3 (2010): 249–72.
[3] Eric Kit-wai Ma, Desiring Hong Kong, Consuming South China Transborder Cultural Politics, 1970–201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
[4] Florence Mok. “Public Opinion Polls and Covert Colonialism in British Hong Kong.” China information 33, no. 1 (2019): 66–87.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僅代表作者本人,並不反映VMAC的觀點。)

員工短評
從《鮑藹倫檔案》看錄像組織的歷史閃光
亞洲藝術文獻庫在2022年底發佈了《鮑藹倫檔案》(下稱《鮑》),截至現時(2023年10月)為止,《鮑》記錄了超過1000項藝術家的文件。檔案庫中不只有藝術家的作品紀錄,還包括活動照片、講座講稿、各機構活動資料、剪報⋯⋯檔案庫亦不只蒐集了Ellen作為藝術家面向的資料,更展示了她作為策展人、錄像藝術推動者的一面。
在《鮑》之中,存檔條目數量最多的,是「展覽和放映」(277份),其次是「作品」(207份) ,接著就是「機構檔案」(194份)。「機構檔案」記錄有關Ellen曾參與的團體,包括關注實驗電影的愛好者組織火鳥電影會(始於1973年)、積極採用錄像的實驗劇場進念.二十面體(始於1982年)、由鮑氏與馮美華、黄志輝、毛文羽共同創立,以實踐錄像創作為目的的錄映太奇(始於1986年)、率先引入國際錄像和多媒體作品到香港的微波國際藝術節(1996年)、還有關注網絡文化的維基托邦(2010年)、以及策展行政服務公司Inter-Act Arts (2011年)。
如果說由《鮑》可以看到香港近四十年的錄像藝術史的側面,一點都不誇張。
火鳥電影會於1970年代積極推廣獨立電影,在當年普遍觀眾只能接觸主流商業電影的背景下,火鳥透過定期舉辦工作坊、小組討論和放映[1],孕育年青有志的影像創作者,為另類電影(當年常叫實驗電影)提供出路。然後就是眾所周知的故事——鮑藹倫以實習生身份參與火鳥電影會,並把其中一個放映項目命名為Videotage(錄映太奇),為日後的錄像藝術活動種下種子。
進念.二十面體作為實驗劇場先驅,早於八十年代已開始將錄像和投影裝置應用於劇場作品之中。錄映太奇在初創時期,還是藝術家群體(artist collective)時,正是寄居於進念的跑馬地辦公室內,同時為進念的劇場作品做紀錄和錄像創作。這亦影響了Ellen對理解表演、舞蹈和攝影機之間的關係[2],從她的個人作品如《大動作 # 1/10》、《借頭借路II》可見,鏡頭前進出不定的演員,刻意被放慢動作的舞蹈員,都是Ellen思考動作、舞蹈、畫面的實驗。
錄映太奇在1996年獲資助成為獨立藝術機構。同年,錄映太奇首次舉辦國際錄像節「微波錄像節」;雖以錄像為主,但第二屆已改名為「九七微波電子媒體節」,引介以光碟為媒介的創作。其後,微波獨立而成為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奠定其在媒體藝術的發展方向。今天大家都對藝術科技(art-tech)耳熟能詳,其實微波早以開荒牛的姿態率先把媒體藝術 (electronic art, media arts) 帶到香港。
維基托邦和Inter-Act Arts雖然被歸檔為「機構」,但它們其實分別屬於活動項目和小型公司。維基托邦源於錄映太奇2010年的一個項目,以一連串的活動,如主題演講、討論、工作坊等,討論互聯網、開源碼、監視等主題。Inter-Act Arts則是一間專注處理作品製作(production) 和策展的公司。
透過《鮑》所收錄近四十年的資料中,我們可見香港錄像歷史如何由實驗電影會中萌生,蛻變成由愛好者組成的錄像群體(collective),發芽並分支為不同媒體取向的藝術節,其後涉足更專業和集中的學術討論。當然《鮑》只代表了香港錄像史的其中一面,蔡甘銓和鄭智雄創辦的錄像力量、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ifva」、由城市當代舞蹈團主辦的「跳格— 香港國際舞蹈影像節」也見證著香港動態影像的變遷。
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翁子健於六月舉行的「認識鮑藹倫檔案」講座中提及,「一般而言,人物檔案會要求檔案完整性 (archival integrity)」,但研究隊伍鑑於Ellen是位仍然活躍的藝術家,她的收藏仍會不斷變動,加上她的私人收藏量龐大,他們只能在眾多文件中作出選擇。」
數量龐大且千絲萬縷的文件,要如何收集、整理、建檔,必然充滿困難。好些重要的錄像展覽及放映活動在《鮑》的檔案中雖可見其踪影,但若要仔細考據和調查,不少細節仍有待補充。以1986年舉行的「另類電映・錄映節」為例,莫說香港部分的作品有沒有迭失的問題,我們甚至無法得知所有放映作品的名字,很多消失了的細節都可能已經無從考據。
近四十年的錄像歷史,不算是很久以前的事,但不少的空白,仍尚待填補。《鮑藹倫檔案》中的「機構檔案」擁有過往重要節目的關鍵字,而每個霎眼而去的名字、作品和展覽標題,都是研究員必需以銳利目光捉緊的歷史線索。
[1] 活動內容詳見《鮑藹倫檔案》機構檔案——《火鳥電影會實驗電影工作坊》
[2] 《【我的藝術影響】 03 Ellen Pau 回看受過的藝術影響》,《信報》,何兆彬,2019年 3月25日。https://lj.hkej.com/lj/article?id=2090988。

員工精選
OK. Video Festival, 2003
第一屆O.K.Video錄像藝術節是由印尼藝術家群體ruangrupa與印度尼西亞國家畫廊合辦。作為雅加達首個錄像藝術節,它們不但舉辦展覽,還有一系列的藝術家分享會、工作坊、研討會⋯⋯
錄映太奇在該年的「特別放映」中,播放了《錄影太奇最佳作品第六集——星際都市》;同場的參與團體,還有來自南非的Pulse和日本的Videoart Center Tokyo(VCTokyo)。
《星際都市》的錄像作品除了拍攝城市面貌和當下處境,還呈現藝術家的感受和反思。VCTokyo也不約而同地播放了九齣以「城市」為題的短片。兩所來自不同地方的機構,以同一主題作放映,不禁令人好奇當年千禧之初,不同國家與城市的藝術家如何回應歷史和想像未來。
有關錄映太奇庫藏通訊
錄映太奇的收藏見證著香港過去三十五年的錄像及媒體文化發展。庫藏作品來自不同背景的藝術家,涵蓋範圍由短篇電影、錄像文章、實驗錄像以至動畫等各種類型。《錄映太奇庫藏通訊》讓大家了解媒體藝術及其保存的最新發展狀況,並介紹庫藏的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