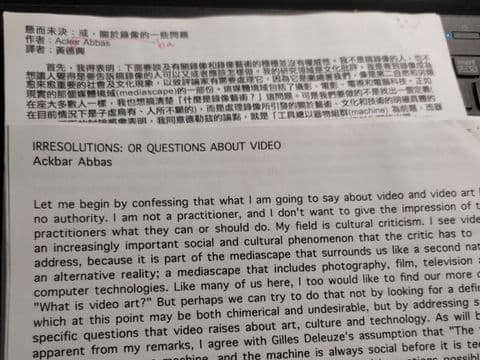October 2022
VMAC文章
《懸而未決:或,關於錄像的一些問題》
作者:Ackba Abbas
譯者:黃德興
校譯:黃小燕
首先,我得表明:下面談到錄像和錄像藝術的種種,並沒有權威性。我不是搞錄像的,不想讓人覺得我要告訴搞錄像的,可以又或者應該怎樣做。我的研究領域是文化批評。我認為錄像是愈來愈重要的社會及文化現象,以致評論家有需要處理它,因為,它是媒體景觀(mediascape)的一部分,而媒體早已圍繞著我們,尤如第二自然和另類現實。這裡說的媒體景觀包括了攝影、電影、電視和電腦科技。正如大多數人一樣,我也想搞清楚,「錄像藝術是甚麼?」這個問題。可是,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找出一個定義,因為,定義可能既不切實際又不可取,而是去處理錄像所涉及的關於藝術、文化和技術的具體問題。下面的討論將會表明,我同意德勒兹的說法,就是「工具總以機器為前提,而機器在技術之前,總是社會的。」即是説,是社會和文化條件讓技術革新成為可能。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錄像藝術的文化位置。有人説它已經有能力動搖,甚至取代,舊的藝術形式。在20世紀30年代,攝影家/理論家納吉(Moholy Nagy)有一陣子很樂觀地説,未來的文盲不再是不能讀或不能寫的人,而是不能拍照的人。1965年,「錄像之父」白南隼用同樣的語調發表這番著名的言論:「正如拼貼取代油彩一樣,陰極射管將取代畫布。」我們現在知道,這些帶有預言色彩的說法並沒有實現,也不大可能實現。錄像不會取代油畫、攝影或電影。認為它會的話,就是將科技的進步和藝術的進步混為一談。「新科技淘汰舊科技,所以新藝術淘汰舊藝術」一類的論証,是錯誤的演繹推論。
這就帶出一個相關問題:藝術與科技的關係。白南隼的陳述也有一定的意義,如果他的意思是,今天,藝術不可能忽視科技,我們活在一個電子和數碼複製的年代。以這種方式閱讀,它就無涉甚麼進步理論。相反,它提醒我們,科技有能力引入新的觀察方式,或者新的視覺機制(regimes of the visible),與舊有的機制相互作用、衝突和共存。那麼説,錄像(以及現時的數碼)影像會為我們的視覺清單增添新選項。除了從繪畫到電影的視覺史(history of visuality)已經創造性地探索過那些可見的、不可見的和半可見的影像,現在還要加上:快速可見的,即「實時」的電子視訊影像;以及「猥瑣的」,高解像度的(high-resolution),超真實(hyperreal)的影像。電子視訊和超真實都挑戰了我們對時空的理解。高科技方案(high-tech resolution)也會導致其自身種種的文化懸而未解(irresolutions):這是錄像的啟示。重要的是:定義錄像的,既是它的技術屬性,也是它的社會和文化用途。再者,先進的科技並不就是先進的文化。然而,各種視覺機制已經多到我們不能處理的地步,引起了極大混亂。在我看來,錄像藝術之所以重要和令人興奮,正在於它介入這些機制的方式。
我的下一個問題,涉及錄像與時間的關係,把技術和文化的問題連結起來。在時間問題上,錄像可以與電影明確區分開來。敘事電影中的時間常常是再現的(represented)時間,不管那是五十年還是一天,抑或像希治閣的《繩索》這罕有的例子那樣,行動的時間跟觀看的時間是一樣的。相比之下,錄像的時間則似乎是在兩種時間之間交替:一方面,它根據真實的時間,即頃刻的時間、或即場的時間來運作;另一方面,它是不確定的時間,它從現成的錄影帶中拼合影像,好像電影一樣。因此,電影的時間每每是再現的時間,而錄像的時間,不管是上述那種情况,可謂屬於展演的時間(time of performance)。如是看,錄像比電影更接近舞蹈。舞蹈和錄像的緊密關連並非偶然。舞蹈關乎速度和運動,而錄像可以比電影更能隨時改變播放速度或靜止鏡頭。正因如此,當電影要展示為速度科技(technologies of speed)所改變的當代都市面貌時,傾向借用錄像變速和靜鏡的技巧。本地導演王家衛的《重慶森林》是上佳的例子。同理,錄像跟時裝也有密切關係。只有錄像能帶出這個事實:時裝的時間也是展演的時間。無怪乎,在一部要同時帶出都市和時裝其難以捉摸的特質的電影——温達斯的《城市時裝速記》,就要用錄像來補充電影。説到底,正是錄像的這種展演性,使一門裝置藝術得以生成:錄像裝置。在錄像裝置中,錄像螢幕隨物成物,極致地發揮它的展演性,盡管它自成一類。
至於錄像跟聲音的關係,是極具啟發性的問題。法國學者米修.仕昂(Michel Chion)在討論錄像藝術家希爾(Gary Hill)的作品等課題時,精辟地提出這個問題。仕昂首先指出,錄像藝術家除了補上中性的背景音樂或人聲外,就通常不知道該怎樣處理聲音。然而,當中的原因卻帶出了錄像的有趣之處。仕昂指出錄像遠較電影容易加速,事實上快到可以跟上文本的速度。希爾做的,是「把講述的文本跟同步的影像並置對質」,如是,所有關乎聲音的一切都已經置於錄像影像之中,並複錄在那裡,因此聲音是多餘的。希爾的錄像要我們用眼睛去聽。仕昂談到MTV時,也有同樣的觀點(這裡也順帶提出,錄像藝術並非只有藝術錄像,也包括電視和MTV)。MTV快速的影像串聯,令影像本身俱有原聲軌(soundtrack)的某些特性。正如原聲帶將文字、噪音和音樂混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同時聽到它們,MTV個別影像的快速串聯,讓觀眾的記憶仿似一台理想的影像混合器般運作,把個別的影像調成複調視覺(visual polyphony)。就這樣,MTV,作為一種容許我們心不在焉地觀看的「選擇性影像電視節目」,解放了我們的眼睛。這也是錄像藝術的目的。
討論過錄像時間和錄像聲音,我要提出最後一個問題。錄像似乎日益取代了照片作為真實證擄的媒介。我們現在用婚禮錄影來取代婚禮照片。案發現場照片的權威性讓位於隱閉的攝錄機所拍到的錄影帶。可是,用錄像作為證據跟照片一樣含糊。巴特(Barthes)説過,照片是「確切但隱遁的證詞」。錄像也是一樣。錄像作供的含糊性的知名案例,是一名過路人拍攝到 Rodney King 被洛杉磯警方毆打的錄影帶。看到影帶的第一個陪審團判定警方無罪,結果令人驚訝,因為,那盤影帶是根據辯方律師的特定指示而播放。在重審時,第二個陪審團推翻了之前的裁決,因為這一次,影帶是以不同的方式,放在不同的證據脈絡中展示。這個例子頗能説明錄像的懸而未决,它的意涵,一如其他文化產物,受到意識型態所操弄。
可是,對於錄像和意義的關係也有另一個思考方向。這是温斯達在一篇短文中提到的。文中他描述他是怎樣在電視上隨意轉台來看電影,結果賦予了電影某些錄像的感覺和質感。温達斯這樣描述:
電影中有些片段突然變得出奇地直接,或具體得令人動容,以致你屏息靜氣,或危襟正坐,或掩口結舌……
這個現象純屬偶然,尤其是當你在看電視。你轉到另一頻道,畫面出現:暮色空街的場景,街燈剛照進來,燈光閃動的汽車進入鏡頭,背景中,一個女人牽著狗從房子裡走出來。鏡頭緩緩淡出,螢幕變黑。你看到的,已經是電影的結尾,影像簡單明確不過,也不帶任何意思,因為,你沒有看到帶出這幕的鏡頭。(Emotion Pictures 52, 53)
温達斯要喚起的,我看似乎是錄像影像最有力、最打動人的特質。錄像通常沒有讓我們知道「帶出這幕的鏡頭」。影像沒有被刻述(inscribed)在一套涵義之中;相反,它去描述(describe),或者更好的説,是解述(de-scribe)。藉著解述而不是刻述,影像從固定的意義脈絡中得到解套,卻不會因而變得毫無意義。我們可能要這樣問:這種神奇的技藝究竟是怎樣達致的?這一點,我們要參看錄像製作者的工作,因為,他們一直努力探索可見性(visibility)和意義的界限。無可超越的白南隼已經説過:「錄像:不是,我看,而是,我飛。」或者,錄像藝術一個像其他一樣好的定義是:一種不怕飛的藝術。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僅代表作者本人,並不反映VMAC的觀點。)
編注: 我們最近整理VMAC的倉庫時,發現了文化研究學者阿巴斯教授的一篇文章,一份噴墨打印稿,文章取題「懸而未決:或,關於錄像的一些問題」。經了解,這篇文章大概是在千禧之初,由錄映太奇委託撰寫。文章寫得深入淺出,剖析錄像(藝術)如何更新我們的視覺機制運作,並觸及錄像的若干核心問題:錄像的時間、錄像作為證據的含糊性、MTV是怎樣「用眼睛去聽」的,以至,錄像如何調度影像的層層意義……
本文經作者授權重刊。

錄映太奇自家出品《The Best of Videotage》系列,在錄影帶盛行的年代,一共出版及發行過六輯。第一輯以《失去又尋回》為主題,探索後殖民的身份認同,收錄11位藝術家在八、九十年代的迷失與尋索。我們現在整理錄映太奇的各樣檔案,彷彿也是一場失去又尋回的經歷。
有關錄映太奇庫藏通訊
錄映太奇的收藏見證著香港過去三十五年的錄像及媒體文化發展。庫藏作品來自不同背景的藝術家,涵蓋範圍由短篇電影、錄像文章、實驗錄像以至動畫等各種類型。《錄映太奇庫藏通訊》讓大家了解媒體藝術及其保存的最新發展狀況,並介紹庫藏的亮點。